周云天展开手掌,铜钱安稳地躺在掌心,从小便在窑坊劳作,周云天的手掌饱经磨砺,今天这粗粝的掌纹,反倒是把铜钱托得更玲珑润泽。
“这是我今日最大的事,也是我今年最大的事,总算是完成了。天哥,还有一年的光阴,你和小姐的事,一定能如你俩的愿的。”瓷宝双手合十,做了个“上天保佑”的动作。
告别瓷宝,周云天继续朝新河的方向走去。一侧江水奔流了千百万年,另一侧岸边垂柳正冒出新芽;江中孤屿郁郁葱葱,中间露出佛寺外墙的一抹金黄。雾气在对岸山间涌动,犹如惬意舒展的巨龙,搅动阵阵暖风,把人吹得心悦神怡。
铜钱还在手中,周云天的脑海中浮现出那张脸来:眼睛如同阳光浅落的深潭,嘴角总是挂着读懂人心的聪慧之笑,脸蛋光洁得让他羞愧。——哪怕他周云天是瓯窑奇才,所打造出来的旷世珍品,都无法及她容颜的万分之一。
把这样的脸庞烙在心底,这世间再好的颜色都会黯淡。何况并不只有皮囊,周云天与这位“小姐”的缘分,在岁月中烙下过彼此相携、欢笑流泪、出生入死的深刻印记。
在暖风中行走,往事也如云气,在周云天的胸壑间,悠悠地荡了开来。
与此同时,位于向麓城万花塘的郑家大宅前,郑擎亭的马车也已停到门口。
郑家家丁头子吕水龙早已携众家丁在门口迎接,一条红毯从下马处铺至内院,郑擎亭下得马车来。吕水龙便高喊一声:
“擎亭公踏红归家!”
迈入向麓城最高最大的郑家大门,庭院内亭台轩榭错落有致,假山池沼堆砌其间,名树名花点缀映衬。这番盛景,曾让每一个踏足此地的人都心生恍惚:这莫不是到了姑苏城?
大院之中,首个迎接郑擎亭,自然是郑擎亭的儿子郑纲。这位十五岁的青年,在别人眼中简直是天之骄子,含着金汤勺出生的。见到父亲,却是脸色惨白,唇齿嗫嚅,眼神在父亲和郑家特聘的延师张晋元之间来回甩动,最后在张晋元鼓励的眼神下,这才说了一句:
“爹爹好。”
郑擎亭脸色阴沉,皱起眉头,问道:“可有好好读书?”
“读书,是有的。”郑纲口齿不清地回答道。
郑擎亭深吸一口气,重重叹了出去,每当此时,他都会忍不住想:“为何我郑擎亭英明神武,冠绝一方,却生出这么个儿子,还不如一个小小窑匠!”
他心中想着周云天和他的手艺,耳畔已经响起环佩叮当之声,郑家的女儿们齐齐走了出来,“爹爹”的叫唤,如风打榕叶般参差鸣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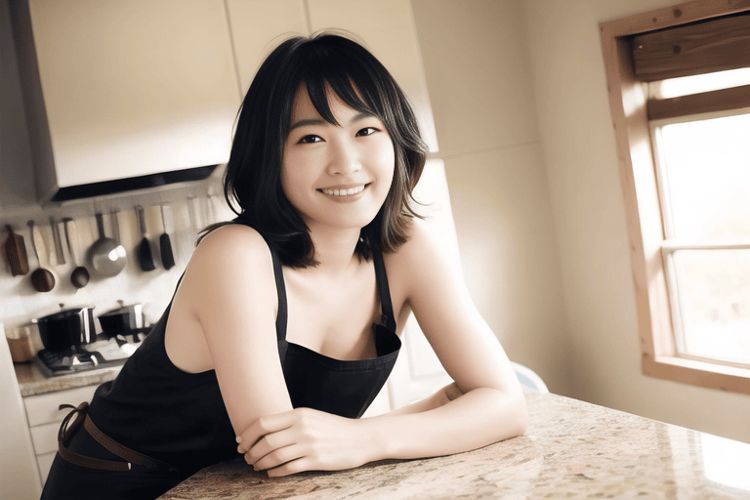
“爹爹,家中一切都好。纲弟弟也有很大的长进。”一个稳且柔的声音响起,其他的女儿们便不说话了。
郑擎亭望向长女,不知不觉间,长女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。她站在那儿,如同一座玉色的山壁,初见大气典雅,细观顾盼神飞。这位长女虽然平常并不出门抛头露面,但向麓城坊间一直有“郑家长女是天女下凡”的传闻。
众多子女中,只有这位长女,能让郑擎亭看到自己年轻时的风采。但郑擎亭并不会在众人面前,表现出对长女的偏爱。听到长女这么说,他也只是点了点。继续朝屋里走去,只是经过几位女儿的面前时,他停下脚步,转头过来问长女:
“沉芗,他们都带着自己的丫鬟,你怎么孤身一人?你的丫鬟瓷宝呢?”
“回报爹爹,我吩咐瓷宝出门办事了。”
“不要纵容你的丫鬟了。丫鬟的名声,也是你的名声。”
说罢,郑擎亭走进自己的书斋。
坐在熟悉的罗汉榻上,郑擎亭这才有放松之感,这几日又是车马劳顿,又周旋于官场商场,都是为了那件横空出世的瓯窑。接下来,他得开始好好思考,如何用周云天的手艺,为自己赚取更多的银子。
新河窑坊,周云天的脸,女儿沉芗的脸在他的脑海中一一浮现,他渐渐坠入梦乡。
恍恍惚惚间,郑擎亭又回到了那个地方——
无处不在的焦味让人心神惊慌,很快便能看到冲天的黑色烟柱,火借风势越烧越大,火焰猎猎声,巨木倒塌声,惨厉的呼救声不绝于耳。转瞬之间,天又降下豪雨,那已被烧成焦土的大宅,像个黑黝黝的恐怖深洞,不断地向外流着黑色的水。一位身材高大却被雨水打得佝偻起身子的人,怀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女婴,背对着黑洞大宅,一步一步地,行走在江畔泥泞的道路上。
这是郑擎亭最黑暗、最悲惨的时光:一场莫名而起的大火,烧毁了他少年得志后,意气风发纵横商场苦心经营的一切:父母、发妻、家丁、宅子、财富...他唯一救出的,就是自己的女儿:沉芗。
一阵风吹来,他发现自己行走在瓯江畔,他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,还要继续往前走多久。他已经感受不到脚是否存在,只有襁褓中女儿软糯的脸蛋,让他有一丝尚且存活的感觉。
江水滔滔,这人间竟如此苦楚,不如一跃而下,了却此生,落个解脱吧。
这样想着,襁褓中的女儿却开始咿咿呀呀起来。
那声音毫无悲苦之色,竟如此动听。
江水声与女儿的咿呀声,就像两股力量,把郑擎亭在地府与人间来回拉扯。
一座残破的庙宇出现在路边,郑擎亭再也走不动了,他迈入几乎全烂了的庙门,在门边靠着墙壁,滑坐了下去,顺势朝前望去。
这一望不要紧,眼前之所见,让他的头皮耸了一耸。
那破庙小小的院子内,在四处疯长的野草中,立着一个又一个泥塑的小人。
那些小人姿态各异,有的呆坐,有的练武,有的和另一位小人依偎着,还有的甚至挂在一些粗壮的草上,仿佛要飞升。
正在郑擎亭吃惊眼前为何会出现这一幕时,从佛堂中走出一个黑乎乎的事物来。
之所以说是“事物”,因为个头矮小,不像成年人。
“莫非是土地公。”郑擎亭脑子一片混乱着,那“事物”已经来到跟前。
定睛看清,来者居然是一个约莫三、四岁的孩童,一个以干草做成衣物,且全身沾满黑泥的孩童。
郑擎亭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,怀中的沉芗却放声大哭了起来。
郑擎亭下意识地去哄,沉芗却越哭越大声。
那黑泥男孩见状,转头爬上了一颗芭蕉树,取下一片大的芭蕉叶托举在手中。郑擎亭瞬间明白了他是何意,便把沉芗放在了芭蕉叶上。黑泥男孩便对着沉芗,唱起一首歌谣来:
“阿娒汪汪,阿妈纺纱,阿爸赚铜钿,阿哥摘落茄...”
郑擎亭不禁落下泪来,这场变故发生之前,他听到发妻最后的声音,便是哼唱此歌谣,哄沉芗睡觉。
听到这个曲子,沉芗停止了哭闹。她躺在芭蕉叶上,芭蕉叶被黑泥男孩小心翼翼地捧着。黑泥男孩轻轻摇晃,沉芗看着黑泥男孩的脸,不多时,竟面露笑容睡着了。
黑泥男孩轻轻把芭蕉叶抱起,向佛堂走去。郑擎亭如坠梦中般跟了上去,佛堂中的大佛面容伟岸、神色慈悲,身体却已破败不堪,胸口更是有一大洞。香火桌下有个厚实的草垫。黑泥男孩把沉芗轻轻地放在草甸上。又转过头来,从怀中掏出一物,递到郑擎亭面前。
郑擎亭低头一看:一枚铜钱!
上面镌刻四个熠熠发光的“大观通宝”!

![「江山梦密码」后续已完结_[周云天李墨梅]精彩章节免费试读](https://image-cdn.iyykj.cn/2408/55060ec2b3964d8f95f13d53ceff5507.jpg)